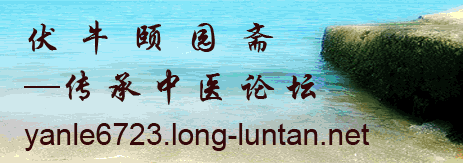“凡十一藏所取决于胆”别论
作者:伯龙
在阐述这个问题前,我们有必要先厘清中医中许多不确切的概念,不然,讨论起来未免云遮雾绕!
一、藏府知多少
中医经典中向来多称“五藏六府”,并且诸多篇章亦多只论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肾五藏,并附以一系列相关的“五”类,如五体、五液、五官、五化、五音、五时、五谷、五果、五畜等等。
而《难经三十九难》曰:藏唯有五,府独有六者,何也?然:所以府有六者,谓三焦也。有原气之别使焉,主持诸气,有名而无形,其经属少阳,此外府也。故言,府有六焉。
简言之,三焦只不过是个空名。它似乎为后起,且为凑六府之数。
更有可怪者,《难经》时代的医经还有五府六藏说.
《四十难》曰:经言府有五,藏有六者,何也?然:六府者,止有五府也。五藏亦有六者,谓肾有两藏也。其左者为肾,右为命门。命门者,谓精神之所舍也。男子以藏精,女子以系胞,其气与肾通,故言藏有六也。府有五者,何也?然:五藏各一府,三焦亦是一府,然不属五藏,故言府有五焉.
看来,在五藏六府和六藏五府两说之间,《难经》没有解决到底哪一说正确。其作者也没有采取折衷办法,干脆说五藏五府或者六藏六府.
而《素问·灵兰秘典》却有“十二藏”(六藏六府)之名,中多一藏“膻中”。不过后人不太在意,一直只说“五藏”。
在《灵枢·经脉》篇中,十二经脉之名皆冠以藏府之名,联系本藏府用“属”,与相表里的藏府联系用“络”。这一点没有疑义。但是前贤还是忽略了其中有两藏特殊。其一就是“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,起于胸中,出属心包络”,因此依照惯例,当有第六藏,并且名“心包络”。
对比《灵枢·经脉》和《素问·灵兰秘典》,后世医家认定“膻中”即是指“心包络”,这似乎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,当无疑义。但是它们实际上并非相同,并有主次之分——膻中为主,心包络为次,另外还存在着“心主”何指?以及到底是“心包”还是“心包络”等问题。
医界向来以为“心主”之意为“心之所主”,因为《灵枢·邪客篇》有文:“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……诸邪之在心,皆在于心包络。包络者,心主之脉也”。文中“心主”似乎就是“心之所主”之意。并且皆将“心包络”认定为“包心之脂膜”。因此“膻中者,心主之宫城也”即与《灵枢·邪客篇》文义相同。
然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,由于医家错注“心主”为“心之所主”,而导致“心主”之义湮没千载。不知《难经》中对“心主”的介绍,明系区别于“心”藏,所谓“心主与三焦相表里,俱有名无形”。而依此句之意,“心主”当是与第六府——“三焦”相表里的第六藏。然而如此一来“心包络”又作何说?而《难经》又奇怪地提出“命门”(依其文乃指右肾)为第六藏,真是疑虑重重!!
其实人们是忽略了《难经》中还有一句很重要的提示,“手厥阴者,心主与手少阴之别脉也”。也就是说“手厥阴心包络脉”是“心主”与“手少阴经脉”相合而成,然而这又是何意?古人无以释其疑,加之认定“心主”为“心之所主”,故忽此句而不论。
也正因为如此,有学者认为“心包络”可能是后人附会“十二地支”之数而添加的,加之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介绍经络的帛书皆只言十一脉——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、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,因此近人更认定“心包经”纯属臆造而附会之脉,或者认为其没有特殊意义。所谓心包受邪而导致的病证与心没有什么区别,因此无独立价值。
其实“手厥阴经”的存在是客观的,它既有正规的详细介绍和穴位,一同其他十一经脉,自然不可能是伪造。即使用后医依“十二地支”之数而补充论,那也只是重新“发现”,绝不是“发明”。
古时所以或传只有十一脉可能有两种原因,其一是此经所连的藏特殊——《难经》言“心主”有名无形,不似其他心肝等藏之易见定形。加之误解“心主”为“心之所主”,而将“心包络”归之乎心经,以为其分支,是故疑而去之。其二者也确实与天干地支的模式相关。如《灵枢·阴阳系日月论》中即将左右手之五经脉分别配以十天干,左右足六经配十二地支。
为很好地适合模式而去手厥阴经而不论,反而使阴阳不齐,看来甚为矛盾,其实这种情况其他篇中也存在。如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》中先论在天之六气“风寒暑湿燥火”,后论在地成形,也是丢失“火”之对应而不论,只论五藏与风寒暑湿燥,如此等等。
那么除《难经》中“手厥阴者,心主与手少阴之别脉也”透露消息外,《内经》中是后否有介绍呢?。其实关于第六藏,《素问·刺禁论》中有一句便是具体的介绍,即“七节之旁,中有小心”,只是因为此句注释莫衷一是,且牵强附会,致使真义湮没。
二、中西类比
要想重新阐释,我们必须参西学而进行类比——这里要着重强调这一点。
中医与西医确实是在不同的思维模式下发展起来的,对人体的认识存在着角度的差异,甚至可以说有浅深之别,但我们不能将问题绝对化,认为两者没有相似可比性,可以各说各的一套而互不在意对方的“反鉴”。其实,中医的藏府观是一种“象”(也即“相”)——是整体中的相对“独立相”,而非“独立质”;而西医的脏腑观是一种“器”(也即“质”观)——是一种“独立的性质物”,这是人为的绝对化(对生动的机械截断),然后又是翻回头强调个体之间的联系。也就是说西医是一种机械的个体观(总体只是个体的总和),而中医却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观,但这却不排除“相对的独立相”——整体中的“全息元”,不然则只是一片未分的混沌。
这也是东西方不同的科学哲学观:东方多谈“象”(也可称为“形”或“相”),而西方则谈“器”,或曰“质”。近年来的科学新观念已经有这种转变,即从物质实体(器)到关系实在(实即“象”)。因此文中我谈中医时用“藏府”两字,西医用“脏腑”两字,以示区别。但是“藏府”与“脏腑”是有相似可比性的。
其实,中医中连属于十二经脉的藏府与通常认为的功能模式藏府是不同的,它仍是有一个固定的“象”,而非仅为一个泛化的抽象模式,要不然如何能被精确地定位描述于经脉的连属中呢?因为抽象模式描述生理、病理没错,却没办法产生线性连属关系。实际上问题在于人体本身上就存在两套系统。一套是经脉中的藏府,一套是西医中的解剖脏腑,而两者(层次又完全不一样)的合并状态才是通常被认定的“功能模式藏府”,关于这一点具体待探讨经络的实质中解释
三、第六藏府之谜
我们知道,在西医生理学中,淋巴管循环是附属于脉管循环的,通常即被认为是脉管循环的一部分。但这只是从纯运动学角度而言的。实际上,淋巴循环是由淋巴器官与淋巴管连接起来的,淋巴循环是淋巴细胞产生与增殖的场所。也就是说它属于人体的免疫系统。如此《难经》所言“手厥阴者,心主与手少阴之别脉也”便容易理解了。
1、心主 也就是说“心主”乃指人体的“免疫系统”,但不仅仅是指淋巴系统,而是广义的“防卫免疫系统”——即白细胞系,包括小噬细胞(中白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)、单核巨噬细胞系(包括神经系统中小胶质细胞、肺内的巨噬细胞、肝中的枯否氏细胞、组织中的组织细胞、骨中的破骨细胞及关节中滑囊A型细胞等,无所不在)和淋巴细胞系(T淋巴细胞,B淋巴细胞及NK细胞等)。这三类细胞系广泛散布在人身各处,并无定形可见。因此《难经》言其“有名(有实际功能存在)无形(实无定形易见
2、三焦 所以将其分为三类者,以其确实该分三类。一以防卫为主——小噬细胞,一为防卫兼免疫应答为主——单核巨噬细胞系,一为参与免疫为主——淋巴细胞系。其实也正因为这种缘故,与之相表里的“府”才被称之为“三焦”。而“三焦”实际上相当于三类细胞的活动代谢空间环境——“焦”古作“”即有空之义,即小噬中白细胞主在的血液相关系统、单核巨噬细胞主在的组织液相关系统(疏松结缔组织)和淋巴细胞相关的淋巴液系统,细胞层次即是成纤维细胞、成骨细胞与网状细胞系。而所以将“心主”之三类细胞与“三焦”之三种环境合而称之,亦可从西学之理中得到论证,以三类细胞皆同源出骨髓造血干细胞,而三种环境的细胞都是源于胚胎期中胚层的间充质细胞,只是“异出”——分化有差异的而矣,当然他们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面。
3、膻中与心包络 那么既然如此,何以不言“心主”为第六藏,反而多出一“心包络”之名,又是何意?如果依《灵枢·经脉》中描述十二经脉的句式,经脉联系本藏府用“属”字,联系相表里的藏府用“络”字,那么“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,起于胸中,出属心包络”,那么第六藏当为“心包络”,那么“心主”如何着落,与之相应的“三焦”呢?。
其实上论“手厥阴者,心主与手少阴之别脉也”中,已经透露,因心主为广泛无定形的“防卫免疫系统”,无以与其余肝心等五藏之有形相侔。但实际上它们有一个固定而成形的有形的象——即“膻中”,这就是西医所讲的胸腺,并且特指其中的“血胸屏障”,是故经云“膻中者,心主之宫城也”——即指胸腺作为中枢免疫器官的功能(当然胸腺还是内分泌腺体,其功用另论)——主指T淋巴细胞系。而膻中之名正与此相关,所谓膻中者,即“嬗变于其中”也,乃指此藏变现藏于胸腺内分泌器官中也。而周围免疫器官——淋巴结者,即“心包络”也,其正累累如络也,主指B淋巴细胞系。
而《内经》中同样有关于此“藏”的描述,即《素问·刺禁论》中有言“七节之傍,中有小心”句,此句千古错释。一说“七节”指胸椎第七节,而“小心”或释为“心包”,因心为大主,而心包附于心,故名“小心”。然而心包与第七椎并无多大瓜葛,心包之俞“厥阴俞”在第四椎旁,因此难令人信服。一说“七节”乃指椎体逆数之第七节,也即第二腰椎,中正为“命门”穴,故“小心”即是指命门(赵献可说)。然而逆数椎体不合古法,且第二椎中只是命门穴,而非“命门”,因此亦甚牵强。近人更注“七节”为颈椎,“小心”指其上的“延脑”,然既与“傍”、“中”两字不符,又过于唐突——诸脑何以只论“延髓”?
其实,古称背之椎体,只言“某椎”,而不言“某节”,所谓“七节”者,乃是指连为一体的“七节”胸骨也,而“小心”依据离《内经》年代较近的《太素》名为“志心”甚妥,而“志心”即是“膻中”也(此待后论),胸腺岂不是正位于胸骨之傍中乎?而与之相应的“三焦”(膻中只指免疫淋巴系统,心主的另外两系统不包括在此厥阴经)也从前论的三种环境转而只代表与淋巴细胞相关的淋巴循环系统,而在这种情况下,人体中显示最为重要的部分分布即是“乳糜池”。我们知道,乳糜池是胸导管的下端膨大,位于第一或二腰椎体前方(恰又与三焦俞平),它收集全身5/6的淋巴,由左右腰干及肠干汇合成;基本上收集左上半身及整个下半身的淋巴;另外小部分右上半身由右淋巴导管汇入右静脉角。相比之下,主次显而易见。然而三焦的具体内容还当另文细论,它与经络的实质密切相关。
4、“六”之数 因为错解“心主”之意而漏失第六藏“膻中”,所以古人在有些情况下附合“三焦”或“胆”以与五藏相配。流传甚广的“六字诀”(最早见于梁朝陶弘景《养性延命录》,后世多有转载):嘘、呵、呼、呬、吹、嘻,分别治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与三焦之实证,有时三焦或代之以胆(如明·龚居中的《红炉点雪》),是岂不奇怪?
按理自当言藏或言府,皆当统一,而此五藏之外另附一府(或三焦或胆),殊为不类。
同样在道教典籍《黄庭内景经·心神章第八》云:“心神丹元字守灵;肺神浩华字虚成;肝神龙烟字含明,翳郁道烟主浊清;肾神玄冥字育婴;脾神常在字魂停;胆神龙曜字威明”,显然亦是将五藏与一府——胆共论,甚为不类。
其实所有的错误都是将“膻中”误以为“胆(古作膽)中”——也即“胆之中”,这可能是后贤解剖粗糙,不知有此物的存在,虽然前贤留有“膻中”之名(因此“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,起于胸中,出属心包络”中的“胸中”可能最初也为“膻中”),但后人多以为其只指穴位或为胸中的代名词,不知具体所指,故此误改“膻中”为“胆”,因此才有后世流传之谬。
而《素问·刺禁论》中并非没有提到“膻中”一藏:黄帝问曰:愿闻禁数。岐伯对曰:藏有要害,不可不察。肝生于左,肺藏于右;心部于表,肾治于里;鬲肓之上,中有父母;七节之旁,中有小(志)心。”只不过说得隐蔽些(连同“膈肓之上,中有父母”一样),言其为“志心”,因此后文中提的“中膻中”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,只不过后人误以为“中胆中”,因此并其后文而改之。
而在古桂本《伤寒杂病论》中,将论五藏之“藏结”与“结胸”并提。实际上就是“膻中”之藏的“藏结”!只不过,此藏特殊而矣。并且“结胸”病确实为“膻中”之病——本当外邪在表,由小噬细胞系对抗,但是因为“下早”虚后,致使外邪直趋“内宫”而致T淋巴细胞系免疫应激,产生自身免疫反应,从而导致局限或广泛的内藏炎性反应,乃至溃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后果——溃疡穿孔!
由是而观之,六藏之中,以膈为界,三藏在上,三藏在下,经中称心为阳中之太阳,肺为阳中之少阴,肝为阴中之少阳,肾为阴中之太阴,而脾则为阴中之至阴,如此依阴阳之理,自然有一藏为阳中之至阳,此即“膻中”也。况且,又有至阳穴,恰巧也位于第七胸椎,与膻中对应,此或许是“七节之傍,中有志心”之另外真意?
其实上古流传多为“六”数,如《周礼·天官冢宰》中提及六谷、六味、六畜之说,六谷为麦、麻、黍、稷、菽及菰,后世漏菰而不论。菰,今称其为茭白,此为嫩茎之名,而其事实方称“菰米”,可供作饭食之用,曹植谓“芳菰精稗”(《七启》),可见其香脆可口。其实,六当指粟、稷、黍、菰、麦、稻(皆禾本科),加麻、菽为八谷。
后世流传较广的对联谓“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”,此文即指豕(猪)、羊、牛、犬、鸡和马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及后世之著作中皆只言前五畜,而不言“马”,此亦一失也。而六味,《周礼·天官冢宰》则指酸、甘、苦、辛、咸和滑;而在藏医中,《月王药诊》、《四部医典》均言六味为酸、甘、苦、辛、咸和涩。一“滑”一“涩”,其实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即有“龙胆草”味为“涩”之说,却无“滑”。那么,哪一个正确呢?笔者认为都对。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与其相应的第六藏特殊的缘故。这一点可以参考梁朝陶弘景真人的《辅行诀藏府用药法式》来说明,此也另文讨论
5、髓 中医向来将“髓”视为“骨髓”与“脑髓”的混合,其实这也是错误混淆的概念“肾”(关于“肾”的问题太多,需另文专门讨论)而导致的混淆,因为“骨髓”与“脑髓”全然是两回事。
大致分析了一些歧义的概念之后,让我们来看看《内经》与《难经》中关于所藏气所舍神有什么疑点。
6、营卫 我们知道,两经典中“营卫”两气皆是并提的,然而何以只有“脾藏营,营舍意”呢?卫气何以不提?又《灵枢·本神》篇中“精神魂魄志意”并提,《灵枢·本藏》篇中竞谓:“志意者,所以御精神,收魂魄,适寒暑,和喜怒者也。”由此可知“志意”当如“营卫”一样,也是相提并论的,并且“志意”两神又高于“精神魂魄”四神,既然“志”不属于肾,“卫”气又漏失,那么本当该如何呢?其实就是“膻中(心包络)藏卫舍志”也!经中一直漏掉这一“藏”而不提,由此我们也可知晓,何以《素问·刺禁论》中言“七节之傍,中有志心”,即将“膻中”称之为“志心”之由了。第六藏不是“右肾”——命门,因此误以为“肾”之神“志”即本当属于真正的第六藏——膻中。
然而“膻中”有否“在体”呢?笔者认为其在体当为“髓”——相当于“骨髓”,我们知道古时有“六极”之病名,除肺极不称“皮极”而称“气极”外,其余皆应“体”名而命之,如脾名“肉极”、肝名“筋极”、心名“脉极”、肾名“骨极”,然尚未有一“精极”或曰“髓极”并无对应,《千金方》中放在“肾”中,然肾已有“骨极”之病名。而《灵枢·经脉》及《千金方》中引扁鹊之言,有“五阴气绝”之说,皆称五体之“死”,而其后则曰:“五阴气绝则目系转,转则目运,目运者,志先死,志死者远一日半则死矣”,独用神“志”之死,显然不侔。其实当是“髓先死”,乃指膻中之气亡也,然此亦正好作膻中之神为“志”的又一论证。而《千金方》中,也是因为如前文中所说的误以为“膻中”为“胆中”,所以在介绍“胆府”时,其后附以“髓虚实”条。实际上述余五体之虚实条皆附在五藏之后,忽然在“胆府”中冒出“髓虚实”,显然同前文所说的误将“胆”混在五藏之中,实际上仍是误将“膻中”——第六藏的“髓虚实”移到“胆府”下。由此亦可佐证,确有第六藏相应之体,也即膻中之在体为“髓”也!
因此,回头看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:帝曰:藏象何如?岐伯曰:心者,生之本,神之变也;其华在面,其充在血脉,为阳中之太阳,通于夏气。肺者,气之本,魄之处也;其华在毛,其充在皮,为阳中之少阴,通于秋气。肾者,主蛰,封藏之本,精之处也;其华在发,其充在骨,为阴中之太阴,通于冬气。肝者,罢极之本也,魂之居也;其华在爪,其充在筋,以生血气,为阴中之少阳,通于春气。脾、胃、大肠、小肠、三焦、膀胱者,仓禀之本,营之居也,名曰器,能化糟粕,转味而入出者也;其华在唇四白,其充在肌,此皆至阴之类,通于土气。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。
在了解了前面所说,此节文字就要澄清,即“至阴之类”包括“胆”在内,不然,依照文中所说:心、肺、肾、肝和脾、胃、大肠、小肠、三焦、膀胱,总共也只有十藏,而实际上十一藏所取决者为“膻中”也。此系后人不识第六藏何物,在至阴之类中取“胆”而移于后,而去“膻中”以为谬,关于这一点辨别五藏六府时已论述过,显然参之西学亦容易理解,免疫功能低下,一切藏府的活动都受影响。而临床上,我们可以观察到,免疫功能低下者,至阳穴出多有压痛!
至此,结论很显然,“凡十一藏所取决于胆”者,千古错谬也,十一藏所取决者为“膻中”也!就是中医中的第六藏,也就是相当于西医所讲的作为中枢免疫器官的“胸腺”(主要指T淋巴细胞)的“功能”!